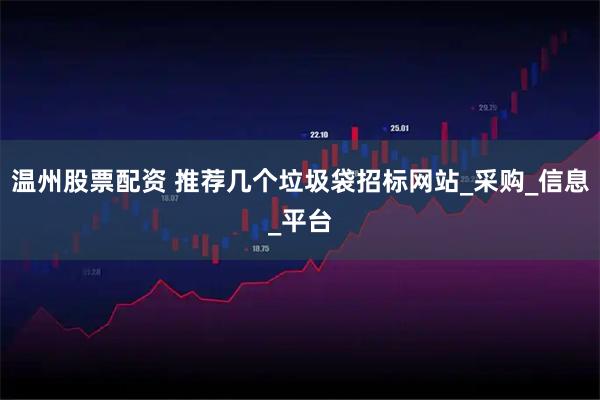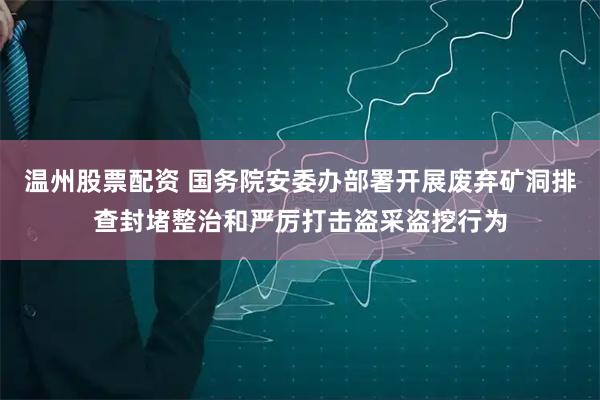2005年初夏,王玉龄端起茶杯笑问:“粟刚兵请我吃饭?行啊温州股票配资,军人何必结仇。”话音一落,客厅里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。
那时的她已77岁,住在上海儿子家里,窗外梧桐叶新绿。江面吹来的潮湿风夹着汽笛声,提醒她自己终于彻底落脚在大陆,而这一刻的闲谈,比起半个世纪前的枪林弹雨,显得格外平和。
时间往回拨。1928年,她出生在长沙书香门第,父亲研究古籍,母亲弹得一手好古琴。独女身份让她从小“饭来张口”,却也养成了倔强脾气——家里越是保护,她越想自己做主。

1945年夏,抗战胜利。17岁的她坐三天火车从贵阳回长沙,“长街灯火好像全为我点亮”,她在日记里这样写。几周后,经好友介绍遇到张灵甫。对方一米八,皮靴锃亮,说话带北方口音。她后来回忆:“那天我就觉得,这个人像舞台中央的探照灯。”
母亲反对,理由很实际:年龄差二十五岁,军人职业凶险。可少女的决定一旦拍板就难再更改。程潜当介绍人,上海金门饭店的婚礼铺张得像场新闻。她记得最清楚的,是张灵甫在飞檐下递给她一朵栀子花,香味浓烈,几乎盖过了军号声。
新婚生活短暂而绚烂。张灵甫担任南京警备司令,两人泛舟秦淮。夫妇合写那首四句小诗,她总觉得自己那两句不如他写得豪迈,可张灵甫偏赞她“韵脚圆”。甜蜜才刚发酵,1947年调令把他推向苏北前线。临行前,他把一把小手枪塞进她手里,低声说:“真到绝境,你带着它。”那支枪,她辗转保存了多年,却未曾扣动扳机。

孟良崮一役,子弹声在山谷里回荡,29岁的张灵甫再也没有回来。关于他是拒降被击毙还是自尽,至今仍争论不断,她只说一句:“他那脾气,认定的事就不会回头。”19岁的她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,穿过满城白布招魂幡,心里一阵空白——这是她最不愿追忆的画面。
1948年底,她随母亲和年幼的儿子登船去了台湾。船舷上风大,她的发梢被吹得打结。岛上的生活远不如想象中体面,抚恤金少得可怜,她就靠教英文补贴家用。夜深了,母亲常叹气:“灵甫若在,哪至于此。”她不吭声,翻开英语词典,硬是把“debit、credit”背得滚瓜烂熟。
三年后,她考进纽约大学会计系,自费留学。异国都市霓虹闪烁,她白天读书、晚上端盘子,肩上既要养家,又要守住某种尊严。不得不说,这段经历让她彻底独立。与此同时,两岸局势渐缓,1973年周恩来总理批示,她得以回长沙探亲。火车沿京广线一路南下,车窗外棉田连绵,她第一次感到生死与政治间其实还有“乡愁”这个柔软词汇。
1997年,69岁的她决定带94岁高龄的母亲回长沙养老。母亲一句“叶落归根”让她放下美国公寓的钥匙。搬家那天恰逢湘江涨水,老人在轮椅上反复念叨“好像回到三十年代”。儿子张道宇则继续留在上海经商。王玉龄挽着母亲的手臂,心里默默盘算:自己也许终会在故土落脚。

2003年,母亲去世。丧事办得简单,只在家祠挂上旧照。亲友来吊唁,有人小声议论张灵甫的往事,她没有阻止——历史本就众说纷纭,她只求一个“安”字。
两年后,她搬到上海,与儿子同住。城市节奏快,晚饭后散步到武康路,她偶尔抬头看梧桐剪影,会突然想起年轻时的南京。就在这个时期,粟裕之侄粟刚兵想借聚餐聊一聊往事。怕尴尬,对方先托共同朋友打探。那位朋友转达:“他担心您介意。”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答复。
她愿意赴约,不为别的,只因她把战争视作职业行为。她常说:“那一辈将领,无论穿哪种制服,本质都是服从命令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冷,但在她看来正是理解恩怨的钥匙。席间,她与粟刚兵只聊家常,很少提战史。餐后各自道别,她回去翻出一本旧影集,里面夹着张灵甫写给她的诗稿。纸页微黄,字迹锋利,她叹了口气,却没有落泪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她的心态也影响了周围人。上海一些退役老兵得知消息,专程上门拜访,她总微笑着说:“我不懂战略,只懂过日子。”简短一句,倒让来客放下了紧绷。试想一下,如果她仍抱怨命运,恐怕许多跨越阵营的对话都不会发生。
晚年,她坚持自己买菜、煲汤,偶尔用英语和小孙子聊天。媒体写稿喜欢用“将门寡妇”“乱世佳人”这样的辞藻,她笑而不语。有人问她对历史是何态度,她抬手比了个水平线:“清楚就好,别陷进去。”这一比划,比千言万语更有力。
至今,她依然住在那栋临街老公寓,客厅墙上没有丈夫的军装照,只有一家三口的彩色合影。问起是否后悔当年一见钟情,她说:“不后悔,人生没得重来。”短短十个字,将半生风雨、跨洋漂泊、阵营更替,一并收束。
世诚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